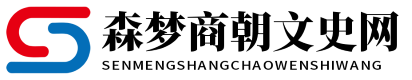晚明时期,文士们似乎不太介意去别人家蹭饭。他们的心灵敏锐,对耻感的反应比其他人强烈,大多数宁愿挨饿也不吃“周粟”。然而,在那个时代,有些文士确实喜欢参加派对和宴席,他们会去财主家白吃白喝,享受丰盛的美食。被款待的人往往显得非常开心,而款待者则笑容满面。这类大型宴请让大家仿佛置身于一个共享、平等的大同世界。

在那时,一些宗室成员如朱承彩,他们虽然有钱,但并不私自积蓄财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邀请文士和妓女来家中饮酒作乐。在中秋节期间,他还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派对,邀请了南京的张献翼等一百二十多位士子,并且叫来了四十多名妓女作为伴侣。即便那些原本能在自己家的喜宴上坐上的贵族,也会选择到这里来蹭饭。他解释说:“家里吃饭哪有跟大家一起吃这么快活?”这样的聚会常常持续通宵达旦,有诗人的诗歌表演、舞者的舞蹈、画家的绘画,无论是献唱还是献技,都无所不包。
王伯稠这样的人物也很普遍。他考过一次科举考试未及格后,就再也不想复读,只是专注于写诗,混迹于酒局。当有派对的时候,不管是否收到了邀请函,他都会带上一张嘴和一副肚皮,然后就去大快朵颐。他虽然来自一个普通家庭,但他却经常不带分文地去别人的家里吃饭,即使是在别人家的喜事或者寿星庆典上也是如此。他总是先闷着头大快朵颐,再走人,没有任何客气或奉承之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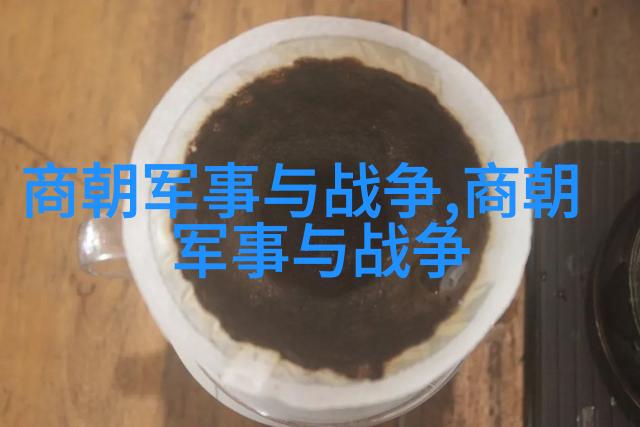
王伯稠曾写过一首关于凤凰的诗,这可能是他自喻吧:“天外有凤凰,独立自徘徊。渴饮沆瀣浆,饥餐昆仑芝。”这些都是他没有自己的,却依然豪迈地吞下的一切。而这种做法,在其他朝代几乎是不见hear的事。但为什么晚明能够出现这样的现象呢?我们无法猜出其中的缘故。
除了王伯稠之外,还有许多像他一样的人物,他们既不参与科举,也不会投身于资本主义萌芽中的商业活动,或是在缙绅之间游走,或是在财主家奔波,或是在写诗卖画中度日,以此维持生计,比如吴扩人,他品行并不低下,而且他的诗名也广为流传,但他却以布衣身份游历缙绅间,与他们交谈,如同钟声一般清脆而优雅。

林春秀是一个自由撰稿人,他生活困难但又爱好豪放,每天都要喝酒。一旦没有酒喝,他就会感到难以忍受,所以每天都要找朋友郑铎借酒喝。郑铎虽然可以赔给他大量金钱,但是林春秀仍旧骂个不停,只因为这个原因,郑铎特地为他制作了一只装饰着“云波”字样的酒杯,用来专门给林春秀用。三十年如一日,这种景象一直持续下去,是什么样的器量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在晚明时期,由于资本主义萌芽,“阀阅之家,不惮为贾”,即便是一般家庭都不惜花费巨资购买书籍和藏书房,那时候商人们与文人的关系相互尊重,因为他们意识到彼此间存在共同利益。此刻,我们只能从历史的角度理解这段纷争与融洽的情景,以及它如何影响了当时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观念。而对于那些傲慢成性的文人们来说,他们通常情形下的傲慢,是由轻视引发的一种行为模式。在那个时代,被轻视成了其存在理由之一,因此才有的傲气,其根源在于是谁看得起谁的问题;而对于官僚阶层来说,则更加看不到这些学者们的价值所在,因此民间开始养起这些学者,让其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不知何方风吹来的李渔家族,每次出门打秋风向路边求讨,将脸色永远保持着淡定,而我们常常讥讽他们,其实这是晚明遗风继续延续的一个缩影;另一方面,如果将金圣叹抢走别人的千金银子的故事放在古代,要想找到类似的例子,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种放浪形骸的情态,在那个严谨高尚的社会环境中根本无法想象。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正反映了晚明民间养士新风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历史阶段乃至整个封建社会末期的一系列变革及其背后的深层次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