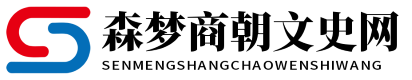作为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的基本史料,商周青铜器铭文由于直出先人手笔,内容涉及册命、典祀、征伐、约契、年历、官制、地理,以及名物制度、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因而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故素为学者所重。自北宋金石之学初兴,士大夫因玩好彝器铭刻而渐致力于补经正史,访求著录之风益盛,研习者常就及身所见,或存之器影,或录以款识,或考辨文辞,或类次名目,其递补摭拾,搜求不舍,数量之众,积甲山齐而有馀。至有清一代,其学冠绝前朝,金文资料已成为研究商周历史与考古的重要文献。然因时代兴废,古代器物如云烟过眼,聚散辗转,隐见靡常,故历千载至今,金文著录之作已数百计。但传统之著录方法多限学者一时之见或一家之藏,致一人之器分载数籍,一器之拓散见诸册,优劣并存,难以汇集,为研究者平添资料检寻和比较的不便。况历代伪器迭出,赝刻不绝,使传世之金文资料良莠杂糅,有待鉴别。宋人著述金文始开风气,用力既勤,搜求亦博,但如《博古图录》之类,所汇商周彝铭不过数百器而已。至清乾隆朝敕纂“西清四鉴”,循《博古图录》遗式,尽管收器数量倍增于前,但伪器充斥,释文舛误,图绘失真,摹铭草率,或本器具铭而不知,或行款错易而不察,书虽后出,学术价值反逊于宋著。乾嘉以来,朴学蓬兴,学者多于经史之外旁涉金石,汇储商周彝铭资料尉然成风,研习考辨之作实非官修可逮。然囿于时见,一家所录之器少止几十,多则数百,远谈不上汇集。晚清至时期,随着对传世及新出彝器铭刻资料的整理研究,网罗日富,水平渐精。如道咸间吴式芬撰《捃古录金文》三卷,虽为未完之作,但独求商周彝铭1334件,且首创以铭文字数多少为次之著录体例,识疑断误,摹刻精善,堪称精博。同光间,方溶益有未竟遗稿《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三十卷,仿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而作,所收商周器1382件,而彝铭逾千,虽间存伪器,但考校尚精。其后刘体智著《善斋吉金录》二八册及《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十八卷,广采各代器物五六千件,其中商周新旧彝铭过半,数量可谓浩繁。然两书虽不乏精品,但伪器杂厕,审鉴欠当。至罗振玉作《三代吉金文存》二十卷,汇求所知商周金文善拓4831件,鉴别精审,询集其时所见殷周金文之大成,影响深远。然而,这些著作或因成书年代早,未及此后出土的大量新资料,或未包括宋代及清代诸著录书中的铭辞摹本,学者早感美中不足,而有增拾补苴,全面荟萃理董殷周铭刻资料的期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世民、陈公柔等先生,在夏鼐先生的指导下集体编纂的《殷周金文集成》(以下简称《集成》),奋力搜集宋代以来之著录、中外博物馆之收藏以及历年各地出土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收器总数近12000件,较《三代吉金文存》增广一倍以上,于1984--1994年由中华书局陆续以珂罗版精印出版,其学术价值之高,影响之巨,有目共睹,已成为学者广泛利用的商周金文文献总集,深受学术界的推崇和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