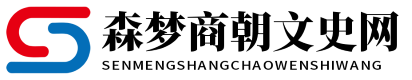在那繁华的晚明时期,文士们以其敏锐的心灵和强烈的耻感,通常宁愿忍饥挨饿,也不愿意接受他人恩赐。然而,这一时代似乎是一个例外,那些文人热衷于参加豪华的宴会,他们不仅爱去财主家蹭饭,还乐此不疲地享受着美食与高雅文化。这些派对常常是隆重而热闹,宾客云集,有的甚至邀请了百余名士子共聚一堂。

有一位名叫朱承彩的人,他家境富裕,却总是慷慨解囊,以款待文士和妓女。在中秋佳节,他举办了一场盛大派对,邀请了南京的一百二十多位才子,一起畅饮海水、品尝美味。此外,还有金銮者这样的豪门,他们原本只需为自己筹备喜宴,但他们更喜欢参加这种大型聚会,因为这样能与众多人一起分享欢乐。
王伯稠是一位才情横溢的人物,他虽然未能考取功名,但他的诗作却深受人们赞赏。他常年混迹酒楼,不论是否有请柬,他总是带上一张口袋和一副肚皮,在别人的家里大快朵颐。即使发布告示让他回家吃饭,也难以唤醒这个忘返之身。

王伯稠这般做派,在那个时代并不罕见。他的一首诗《凤凰》自嘲其身:“天外有凤凰,独立自徘徊。渴饮沆瀣浆,饥餐昆仑芝。”尽管“沆瀣浆”、“昆仑芝”并非他所有,却仍旧贪婪地饮食。这类行为在其他朝代几乎难寻踪影,而晚明为何如此?这是一个谜题,我们无法准确解答。
晚明期间,不仅王伯稠这样的人很多,而且还有许多文人既不追求科举功名,也不会投身商业事业,或是在缙绅间游历,或是在财主家的门庭若市,或是通过写作卖画维持生计,比如吴扩人,这个人品虽好、诗名远扬,却也从来没有因为吃人的嘴短而刻意奉承财主或缙绅,只要有人摆开筵席,无论亲疏,都会毫无愧色地加入进去,并且放言傥论:“花晨月夕,诗坛酒社,宾朋谈宴,声妓会集。”

林春秀是一位自由撰稿人的穷诗人,他每天都需要喝酒才能过日子,所以就去朋友郑铎家蹭酒喝。一旦醉倒,就开始狂乱无序地骂人骂世,即便给他提供酒喝的郑铎也无法阻止。但奇怪的是,这种情况持续三十年,如同一日似今日。而郑铎竟然甘心奉陪,不问出路,无怨无悔,是一种令人敬佩的大度。
晚明时期,与往昔不同的是,那里的资本主义已经萌芽,“阀阅之家,不惮为贾”,即使书籍商毛晋也是文学巨匠,同时又是个书商;著名文学家冯梦龙则既是学者亦兼经纪人。这一切都显示出当时商人们的地位比以前高,而文人们也因此抬高了他们的地位。阳明先生王守仁曾说:“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 商以通货。”将四民平等看待,为富贵者说话也不再有什么尊卑之分。

总体而言,那些傲慢往往源于轻视所致。在那个时代,由于官方对文人的态度冷淡,使得民间不得不接管养士的事务,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国家责任被转嫁到了民间,因此形成了民间养士新风。李渔带着全家的流浪生活向别人借钱借吃,从不脸红羞涩,而我们常笑语相讥,其实,这可能正是晚明遗风所在;清初大家金圣叹到王斫山处弄去了千金银两,说好归还却最后挥霍殆尽,然后把剩下的钱抢白给别人才算数,这种态度若放在前朝简直难以想象,对此可谓继承了晚明养士传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