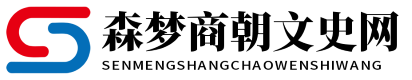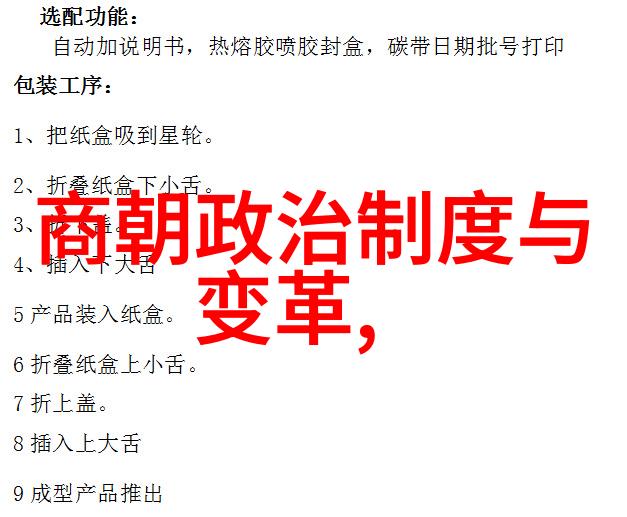比尔·波特有禅者的心,行者的脚,还有一双记者的眼睛。他所行走和记录的地方,都流淌着中国文化的血液,都饱含着那些已经被我们自己遗忘、但在一个外国人眼里却非常优秀的文化基因。
推销自己已经不用了,在中国,这位禅宗的西方传人用一本探访隐士的书—《空谷幽兰》叩开了中国读者的心扉。随后,又陆续推出《禅的行囊》、《黄河之旅》、《心经解读》等。
比尔·波特在《空谷幽兰》告诉人们,隐士并不神秘,只是自我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不论我们身在何处,只要我们心中有桃源,我们就能于低眉间回归桃源,就能找到灵魂的栖息地。
《禅》杂志编委明尧说,他的作品,让中国人感到惭愧。
上世纪70年代,比尔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人类学博士,出于申请奖学金的目的,他决定修学中文。那时,他对中国文化了无兴趣,却歪打正着,比尔第一次发现中国文化“水很深”,有很多“宝贝”。
随后机缘到来。在纽约,比尔与他的第一个中国师父—寿冶老和尚相遇,看到师父刺血写的《华严经》,比尔完全惊呆,第二天,便行了皈依。可是,师父只会说一个英文字watermelon(西瓜),比尔打趣说跟师父学的是“西瓜禅”。
之后,比尔离开美国去了,先是在佛光山小住了一段,上午做功课,下午打篮球,有时还能跟星云法师“合打”。不过,比尔说,大部分时间,星云大师都是站在篮下投球。
佛光山太吵,比尔喜欢安静,于是他又“托钵”到了台北附近的海明寺。那段时间,他“每天打坐三、四个小时,中英文对照看了很多书,中文进步很快”。在海明寺,方丈悟明法师送给比尔一本自己出版的寒山诗集,比尔动了心思,开始动手翻译这位中国唐代著名高僧的诗歌。
对于自己的洋徒弟,悟明法师无教可施。只拿一块木板,敲三下,问,听到没?这是吃饭的意思。
海明寺的岁月,比尔没有向师父提一个问题,可是,他知道,“吃饭很重要” 。确实,吃饭是禅宗的关键词之一,“饿了吃饭,困了睡觉”,强调的是一心不得二用。
“天亮前就起来诵经,夜晚听钟声,一日三餐素食,一个房间、一张床、一顶蚊帐,没有钞票。”这是比尔在《空谷幽兰》中对这段寺院时光的描述。
两年半后,悟明法师劝他出家,比尔觉得自己在庙里“白吃”,又无出家之念,觉得很“丢脸”,于是赶快逃走。
偶然是注定的缘分
师父送给比尔的法号是“胜云”,离开寺庙后,比尔觉得自己应该有一个新名字。一天在巴士里,一幅广告收入眼底,上面写着“黑松赤水”。哇,比尔立刻觉得这个名字很给力。红色是中国人最喜欢的颜色,他索性把黑变成了红。那本译成的寒山诗集就署名“赤松”。这个名字几乎是另一个名字“赤松子”的“脱胎”,而后者是中国上古的仙人,比尔觉得他的翻译一直顺水顺舟,“大概是赤松子在帮助赤松”。
寒山的诗歌译完,比尔又开始翻译元朝僧人石屋的诗。翻译的过程中,对这两位中国古人的兴趣也在与日俱增。在,还有寒山或石屋这样的人住在山里修行吗?这是比尔的兴奋点。
离开寺庙没几年,比尔与一位女子成家,“太太变成师父”。随后又有了孩子,需要上班贴补家用。于是,他在一家英文电台谋到了一个职位,每天把新闻译成英文,每周有半小时的采访。
采访中,他与台塑集团掌门人王永庆的长子王文洋结识并成为朋友,比尔告诉王,他想回寻找隐士,王欣然出资襄助,促成了一段佳话。
终于,比尔如愿以偿来到。一头雾水的他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隐士,只知道,这些人应该住在山上。
一次偶然的机会,净慧法师给比尔指了一个方向:终南山。
“这次偶然是注定的缘分。”比尔说。
于是,他径直去了西安。随便包了一辆车来到终南山下,随便一条路,他便找到了一些修行人。两个月的时间,比尔在终南山四下游方,结识了他梦寐以求的隐士,这些人是他这一辈子见过的“最快乐的人”。
“当时,我就觉得一定要写一本书告诉外国人。”比尔回忆道。于是,他开始动笔写作《空谷幽兰》。
中国的隐士历史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虽然西方也有隐士,但是,西方的隐士是要离开社会,跟社会分开。
“中国的隐士却是社会很主要的一部分,他们去山里的目的是先修好自己,然后出来帮助别人。我觉得这个很了不起。”比尔说。
终南山很深,从北向南约有200公里。比尔第一次进山的时候,山里除了采药的农夫,只有他孤身一人。
比尔告诉外国人,去寺庙好像是读大学,进山是读博士班。小隐于山,大隐于市。要想当大隐士,先要小隐。开始在寺庙修行,达到一定的程度,再去山里盖茅蓬,住几年后再度出山。一般的隐士,三五年之后就下山了,“但是五六个隐士中,总会有一个留下来”。
隐士虽然独居,但是一般都会结伴在一座山上,这样可以互相帮助。刚来的隐士不会过活,老隐士会教给他们一些砍柴、取水之道。老隐士还会传授新隐士一些气功热身抗寒,并告诉他们山里什么东西可以裹腹。
离开终南山后,差不多每两年,比尔经过西安,都要去看望那些茅蓬里的老朋友。有时会在山上看到一两个新茅蓬。老隐士告诉他,通常他们过不了一个冬天。去山里修行先要有基础,因为“那里太寂寞,太辛苦”。
接触隐士之后,比尔发现了他们的不易。而他自称喜欢泡热水澡,吃好东西,过不了如此清苦的生活。
“可是我很钦佩他们,他们很了不起,我望尘莫及。”比尔说。
《空谷幽兰》问世后,隐士和终南山一度成了比尔的标签。在他的书中,所引的中国古文献比比皆是,他笑称自己的文言文比口语还好。
2006年,比尔再赴,从北京一路走到香港,继而推出了另一部作品《禅的行囊》。
在这本书中,比尔追溯了禅宗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他发现,禅宗有几个特点:大家都要住在一起;还有,禅宗起床后就是修行,打坐是修行,洗盘子也是修行,别的宗派不一定重视后者。
禅宗的历史是一部从北向南的历史。比尔从柏林禅寺一路向南,经过少林寺,走到四祖寺、五祖寺,最后到达曹溪的南华寺。
比尔认为,以前的禅宗都是几个人在一起,一个师父带几个,四祖之后,禅宗逐渐在中国发展起来。四祖有500个,他们住在一起,种田养活自己。“从那个时候起,禅宗变成了中国最厉害的一个宗派。”
随后的五祖有1000多个,他把衣钵传给六祖慧能。“虽然受教育不高,但是慧能跑到南部,发展了3000多个。”
《禅的行囊》之后,比尔下一部的著述是达磨祖师传灯印心的宝典《楞伽经》,他花了近三年的时间来“啃”这部即使是中国人也难得搞懂的经典。
在禅宗的法门中泡久了,比尔并不排斥其他的法门,他说,“中国有三个很好的‘门’—儒、释、道。人不可以同时进两个门,只能一门深入。进去后会发现,经过其他的门的人也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