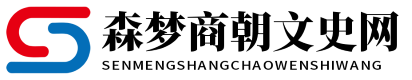李渔,文士确实有脸皮黑厚者,但整体而言,这一阶层之群体人格,是不太爱食嗟来之食的。文士心灵敏锐,其耻感比其他人强烈,大都宁可饿死,也不食周粟。但晚明似乎例外,他们热衷于派对,热衷于财主家去白吃白喝,去吃者雄赳赳气昂昂,放开肚皮大快朵颐,被吃者笑嘻嘻乐呵呵,扩大鼎锅大宴宾客,俨然是熙熙然共食的大同世界。

明宗室后裔朱承彩汗漫使钱,他家里有钱,却不私蓄。隔三差五,他会呼文士、引妓女到他家里去啜饮一顿,一年中秋,他搞了一回大派对,邀请了南京的张献翼等一百二十余士子和马湘兰等四十余名妓佐酒助兴。有金銮者,本来家里办喜宴娶媳妇的,不到家里坐上席,却到这里来蹭饭了。他说:“家里的吃饭哪有蹭饭跟大家一起吃有味啊。”
王伯稠这样的存在在晚明很多,他们既不参加科举,也不顺晚明资产阶级萌芽下海去事产业,或是游走于缙绅间,或是奔趋于财主家的门庭若市,或是写诗卖画,赚几个小钱,与朋友们嬉戏,对这些无所谓,只要能活下去就好,比如吴扩人品并不低下,有诗名却“以布衣游缙绅间”,衣冠白巾,“吐音如钟”。一点也不因为吃人的嘴短刻意奉承财主与缙绅,而是一副傥论:“花晨月夕,诗坛酒社,宾朋谈宴声妓会集。”万历年间的林春秀,是个自由撰稿人,也略有诗名,但家徒四壁,却爱死了喝酒,一日没得那酒,就一日过不得。

这个王伯稠长得一表人才的,有才气勃发,但常常不带分毫到别人家的餐桌上。一上桌都是一个劲地食指大动,只听得见其喉咙里嘎嘎嘎。林春秀也是一位文人,不管自己脸面,都要向别人要酒喝要饭吃,这种做法在当时简直不可思议。而且更奇的是他的朋友郑铎,即便被骂个不停,还不断地给他送酒,并且给他制作了一只专用的酒杯,上面刻着“云波”二字。这份慷慨无求,让人们赞叹。
在晚明时期,由于资本主义萌生,“即阀阅之家,不惮为贾”,商界人物的地位提高,而这也促进了文化艺术的繁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既是亦商亦士,以此类推,如毛晋也是书商兼文学家的身影。而这种情况下,便形成了一种民间养士新风。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即使像清初大家金圣叹一样,无忧无虑地挥霍千金银子,也有人能够轻松接受,因为他们继承了这种文化传统。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理解为什么晚明那些文人的行为看似放荡但又符合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