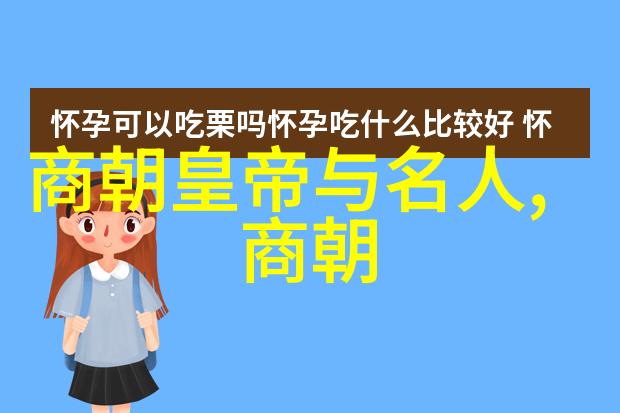我们来探讨历史古籍《晏子春秋》中讲述的这样一则故事:齐景公在牛山游玩,北望其国城而流泪说:“何必滂沱而去此以死?”艾孔、梁丘据都跟着哭泣。然而晏子独自笑着旁边,景公擦干泪水转向晏子询问:“我今日游玩之所以悲伤,是因为孔与据都跟随我而哭泣,而你却独自笑,我为什么会这么做?”晏子回答说:“如果让贤者常守国家,那么太公、桓公将常守;若让勇者常守,那么庄公、灵公将常守。数君将常守,则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由于迭代地占据和离开,使君王也感到悲痛,这是不仁的表现。不仁之君见到这一点,谄媚之臣便多了两分,此即为我所窃笑之处。”

这段对话提醒我们,不仅是普通人,对于死亡,有的人可能更感兴趣或不畏惧,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苦难。在中国文化中,有许多关于“不畏死”精神的典故,如《左传》中的一个类似对话,其中齐景公问晏子:“从古以来没有死亡,它们的快乐又如何呢?”晏子回答道:“从古至今,如果没有死亡,现在享受的快乐,就是古人的快乐了,你作为国王能得到什么呢?从爽鸠氏居住这里开始,一直到季萴继承,再到逢伯陵继承,然后是蒲姑氏继承,最终是太公继承。既然如此,从古至今,没有死亡,那就只是爽鸠氏享有的快乐,而不是你所期望的。”
对于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来说,他们往往更加害怕生命结束,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未能实现全部愿望。历史上有许多皇帝为了求长生不老,不惜采取各种荒诞无稽的手段。而生活艰苦的人们,却往往对死亡持开放态度,因为他们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折磨。

文学作品中也有这样的描绘,如毕飞宇的小说《青衣》,讲述了一位演员筱燕秋因执迷于舞台不能放下而失去了理智,她二十年前因争夺角色差点摔死师傅,但二十年后她依然霸占舞台。这场戏剧化的一幕,让人思考的是,在追求成功时,我们是否应该有个限度?
鲁迅曾经写道:“可惜有一种人,从幼到壮,居然也毫不为奇地过去了;从壮到老,便有点古怪;从老到死,却更异想天开,要占尽少年的道路,吸尽少年空气……”

李国文在晚年发表过类似的感慨,他认为老人应当接受自己的年龄,并尊重他人的评价。他指出,即使是一位资深作家,也应该明白自己的创作已经超越了时代,将来的读者并不需要关心他的现在,只要他过去留下的作品能够被人们记住,就足够了。
最后,他还提到了一个观察,即那些上了年纪但仍旧保持好脾气和风度的大叔大婶,看起来仿佛还保持着些许邪恶光芒,这也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现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