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探讨历史古籍《晏子春秋》中讲述的一则故事:齐景公在牛山游玩,北望其国城而流泪,感慨道:“如果能顺利离开这里而去死,那该多好!”艾孔和梁丘据都跟随着景公落泪。然而,晏子独自一人笑着旁观,景公擦干眼泪后转向晏子问:“今天我出行之所以悲伤,是因为你、孔、及梁丘都跟随我哭泣,你为何却能够保持笑容?”晏子回答说:“如果让贤者长期守护国家,那么太公、桓公也会长久守护;若是让勇者守卫,那么庄公、灵公也会长久守卫。君主因频繁更替而至今才能登位,这种不断更迭和离去,使得君王难以安稳地居住。这便是不仁的表现。不仁之君一见,便有谄媚之臣二人出现,这就是我微笑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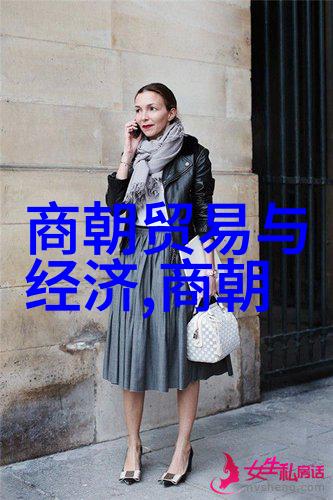
《左传》中也有类似的对话发生,当齐景公询问晏子“从前没有死亡时,它们的快乐又如何”时,晏子回应说:“从前没有死亡,现在的快乐便是古代人的快乐了,而你作为君王,又能得到什么?从爽鸠氏开始居住于此,再经过季萴、逢伯陵及蒲姑氏,每次接班都是太公继承。若果真无死亡,从前的欢愉便是爽鸠氏所享受,而非君王所愿。”
当一个国王执掌大权,他往往不够满足,对生存充满恐惧。他可能求天求地寻找永生,或炼丹采药。但生活艰苦的人,对于死亡反而不那么害怕,因为他们认为生活过于沉重,一死或许是一种解脱,就如同一些人盼星辰下班,有些人却担心退休只好改年纪。

毕飞宇的小说《青衣》中描绘了这样一个人物志——筱燕秋,她因争夺角色A而失去了理智,在二十年前将滚烫开水倒在师傅演员李雪芬脸上。当二十年后的《奔月》再次上演时,筱燕秋继续占据舞台,不给亲传弟子的春来戏台留余地。在复出时,即使筱燕秋已经衣食无忧,但她还是先一步送上了门。她的话语被描述为,“如果我还尊重生活,我必须说,在我的身边,在骨髓里头,在生活的隐蔽处,筱燕秋无处不在。”中国女性特有的韧性使她们在努力做某事的时候,无论身上的气息如何,都洋溢着一种无法挽回命运,还要挣扎的心态,他们那种抑制感痛苦与不甘,让人心碎。
单位里就有一位女士,她成年之后一直未上班,但当领导劝她辞去部门主任职务时,她却坚持己见:我犯了什么错误?我还能干两年的呢!当然,并不是只有女人做这种垂死挣扎的事实,如鲁迅所言,“可惜有一种人,从幼到壮,不免毫不奇怪过去;从壮到老,则有点古怪;从老到死,更异想天开,要占尽少年道路吸尽少年空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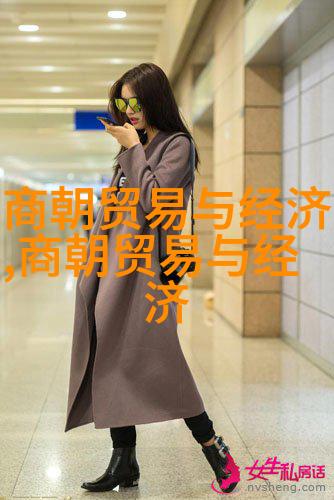
李国文在晚年曾发出了这样的愤慨:“老,就得承认老,就得服老人们尊敬你的年龄尊敬你的资历尊敬你过去的成就尊敬你的好脾气好性格好人缘好风度,不等于尊敬你现在文学状态……明日黄花的事情属于历史,不再属于今天,就没有必要既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了。”
“这世界上最难看的是那些七八十岁先生面对女士一双木然间迸发出邪光的情形。”

(内容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