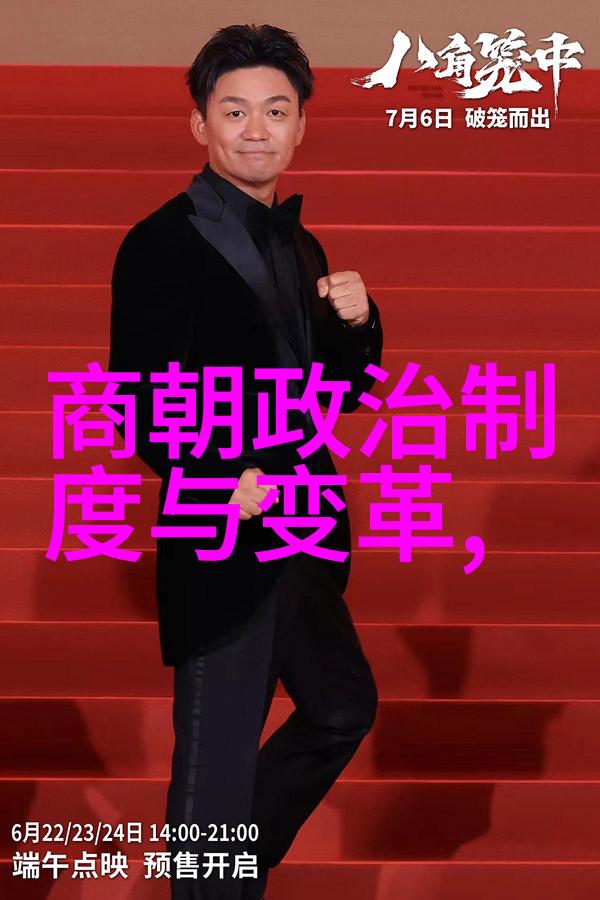我,李桓英,已经满100岁了。早年,我走过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后来,我留下的印记都与中国紧密相连。1921年,我出生在北京,那是一个充满历史和文化的城市。在童年时期,我跟随父母生活在德国柏林,那是一个全新的环境,也是我成长过程中的重要经历。我是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的本科生,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生。在世界卫生组织任职期间,我多次横跨各洲,为贫穷落后地区防治性病和其他疾病而努力。

7年的任期结束后,世界卫生组织希望我续签5年的合同。而我全家已经移居到美国,父母兄弟希望我留在身边。不过,这两个选项都被我排除了。当时,在美国杂志上看到了关于钱学森的报道,他毅然回国的情景深深触动了我的心,让我决定:“时不我待,作为中国人,我很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想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于是,我瞒着家人,从伦敦绕道回来,最终在1958年,当时我37岁,这一年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
1970年,在江苏第一次见到麻风病患者。那一刻,他们带来的痛苦和歧视让我立下誓言,要攻克这场恶疾。1978年,被调到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后,便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这一事业中。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当世界卫生组织着手研究一种联合化疗治疗麻风病新方法时,我开始全国范围内走访调查,并向他们提交了一份详细报告,最终获得免费药品和实验项目支持。我带着这些药品来到云南省勐腊县“麻风寨”,劝说那里每一个麻风病患者服用。这段经历让村民们惊讶:北京来了个女医生,不怕麻风!我们一起喝水,一起吃饭,她拉着我们的手不放。她说:“战士都知道厉害,但上了战场不照样往前冲?麻风菌可没有厉害!”
我的工作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将国际先进治疗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率先开展了短程联合化疗计划,使得全国从11万人减少至不足1万人,而且复发率极低。此后的漫长岁月里,我们一直未曾停止这场斗争。1996年,我们首次提出消除麻風运动,并提出了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模式,被誉为全球最佳治疗行动。

尽管遭遇多次翻车、翻船,以及锁骨摔断等困难,但仍坚持奋斗。我甚至于98岁的时候依然站在第一线,为彻底消灭这个疾病而努力。我曾说:“只有拼搏才能延长生命,而再长的生命如果毫无意义,那就太遗憾。”